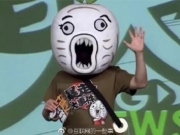唔,李敖先生逝世之际,我先开他一个玩笑。
虽说死者为大,不过以他老人家一向看淡一切的狂生风范,不至于太不敬。
他写了那么多杂文,最明显的表现,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。情绪并非要不得,但是必须同"言之有物"并用、必须跟"大量的资料"并用、必须随"卓越的分析与见解"并用,但他的文章,却情绪有余,其他不足,结果炒出来的,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,反倒没有主菜了。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,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。
总之,中国现代的文人,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。他们的成就,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,而变得不能"恰如其分",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,臃肿而失本来面目。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: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。——嗯,别急,这段不是我说李敖先生的,是李敖先生自己1982年写鲁迅先生的《杂评鲁迅和他孙子》。嘻嘻。

李敖先生写鲁迅先生的这段,有些小问题,其实自己也多少沾染了。他二位都多少被时务杂文,拖累了,或者说,遮盖了点文学创作。或曰,他们警世的文本多了,审美的、叙述性的文本就少了些。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文章本来也不止一种写法。文人不止一种活法。
李敖先生1976年身处牢笼,开始构思的《北京法源寺》,到1991年写完。里头写了19世纪末的激荡思想冲突,写了谭、康、梁等诸位的人生。字里行间,他是更推重谭与梁的。众所周知,康后来保了一辈子皇。梁写了一辈子文章倡导向前看。谭就此殉了理想。后两位,真不算传统知识分子。梁任公自己少年天才,比他师父中举都早,按说是传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,但他一辈子都在用各色文章宣传真理,改革文风;谭则根本来不及立功立德立言,只是用行动,用死亡,“请自嗣同始”。李敖先生一辈子的作为,与梁与谭,甚至与鲁迅先生,有点类似之处。他是行动派,是宣传家。
真正每天骂蒋先生,骂到蹲牢子的人。甚至他的文笔也是。
我以前的朋友里,读过李先生文章的少;但都知道他那句著名的“手淫台湾,意淫大陆”。这话太犀利,太形象,太直白。当然不够传统文学,但说服力很强。——我们熟悉的另一位大人物,很巧的是,跟李敖先生一样喜欢反蒋先生,文笔极佳。佳就佳在,形象生动,便于宣传:“纸老虎”、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、“让蒋先生抗日就像拉毛驴,拉他、推他,再不干就打他”。
李敖先生的文笔,也就是如此了。
他当然有引经据典旁逸斜出的能力,但他给自身定位,并不是个书斋文人,而是梁谭等类似,是个大鸣大放的行动派宣传家。
他这一生,也的确身体力行,做到了。不应天,不顺人,硬到底。多好。
《我看老天爷》里说:
把“天”看得伟大而顺从它、歌颂它、坐待它的恩赐,不如畜养它、控制它、利用它,叫它为人类服务;把天物看成就是那样的,不如用人类的心智去增加它们、改变它们。放弃了人为的力量而指望“天”,那是不合乎“万物之情”的。这样的戡天参天、这样的利用厚生、这样的开物成务、这样的“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”,才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!
真是好文字,好气象!
所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?
一个无法无天的读书写字人。足矣。说再多,怕就要“书生轻议冢中人,冢中笑尔书生气”了。
最后件事。
《北京法源寺》,写的是农历哪年的事,熟读历史者自然知道。那年康梁走了,谭嗣同死了。
今年李敖先生逝世,是农历哪一年来着?
你说巧不巧?
(本文转自张佳玮公众号:张佳玮写字的地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