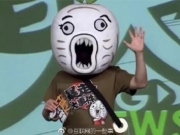“我赚的一半的钱是挨骂的钱”、“技要卖,脸朝外。你都干了这一行,既入江湖,便是薄命人。”
“拍《祖宗十九代》,我很感动的在这:33个超一线的咖,吴秀波、范冰冰、李晨、王宝强、大鹏……这33位真拿我当朋友,说来就来。”
“我跟你说说相声里边打不出1/10的人进入中国电影界,这帮人都得改行。”
采访之前我们还颇有压力。毕竟,除了德云社和纪梵希,郭德纲身上最醒目的标签,是他从来不以和为贵的超强的战斗精神:爱之者奉为嫉恶如仇不揉沙子,恶之者视为睚眦必报反应过度。
结果见到的却是一个满面笑容一团和气的老郭。“你看你们早该来吧。”采访中他强调了两遍。
师父侯耀文在世时曾解释这位弟子的性情成因:“一路坎坷,势必嫉恶如仇”。从籍籍无名到自成门派,个中苦辛,大约能在这一路战天斗地的不服里折射一二。但到现在,以他的地位声名话语权,大众对他的印象,或已从原来的鸡蛋,变成了如今的高墙。

郭德纲在给《祖宗十九代》的演员们讲戏
“我不能承认我是权威。”他警惕地否认了这种预设,“那样的话等于我太俗了。到我死之前我都不愿意做这样一个人。”
但至少,他已经不合适再像过去那样,无所顾忌地选择对手。“拔剑四顾心茫然。”我们调侃。
“怎么拔出来的怎么插回去就是了。”他笑嘻嘻地,“已经不好玩了,(我)怎么说怎么对了。”到现在这个阶段,他觉得自己已无过不去之事:“腾讯都来了,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。”他调侃我们。
“那卓伟呢?”我们调侃他。
“也看开了,也不容易。”
从好战到歇着
“你们原来是不是看了那些宣传报道,觉得我跟土匪一样?”郭德纲问。
“特有战斗精神一人吧。”我们比较含蓄。
“年轻时肯定会那样。”他解释,“现在不是了,没有这么争强好胜了。”
不争强好胜成不了今天的郭德纲。“比如说相声,看人家比咱们强,我得追上他,一定要比他还强,他演了个什么,我也得去学。”他对我们解释过去的心态。“一开始要生存,后来要名利。”毫不避讳。
“名利里其实也包含了自我价值实现。”我们说。
“可以这么理解,但你把它撕开,里面就是名利。”他没有要遮掩的意思。
我们能理解,对当年那个无名小卒而言,名利、地位、话语权,基本属于一整套的打包产品,不可拆分。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你可能五十块钱一场,但人家是腕儿,人家三百一场,差好多倍呢。那我得混好了,得能挣钱,得有知名度,得成为大腕儿。”
这一路力争上游的过程,于我等吃瓜群众,见到的或只是吃相优雅与否,但于当事人,大约并不乏肉搏血战的残酷惨痛。即便在各种自称“看透”、“活明白”的今天,郭德纲忆起当年,我们听着仍是有点咬牙切齿的劲儿。“有多少人后来说告诉你们有一个叫郭德纲的,无论在哪碰见他,一定把这人要摁死,不能让他如何如何:他成了,咱们都完了。你想(这是)我20来岁的时候,业界对我的好评。”
那时候他甚至想过死: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,有家难奔有国难投,真是觉得一身能耐,也没地施展去,连饭都吃不饱。如果街上来一车撞死我,多幸福。我20几岁就这样想过。”
早年间除了说相声,郭德纲还做编剧、参加综艺。2003年,他参加真人秀,在透明的商场橱窗里生活——或者说,展览——了48小时。这种“被围观”的颇无尊严的感觉使他中途情绪崩溃要求退出,“这不是人干的”——但出来后看到观众贴的鼓励纸条,他哽咽着又回到了橱窗。

录制“橱窗真人秀”的郭德纲
开口饭与自尊心,多少是矛盾的关系,而郭德纲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。那个他争了很多年的资源打包里,其实含着他不便强调,又耿耿于心的一点:尊严。
说起来他极为通透:“我赚的一半的钱是挨骂的钱”、“技要卖,脸朝外。你都干了这一行,既入江湖,便是薄命人。”但以外界公论,郭德纲相声最精彩、最见才华的部分,还是在他对批评的犀利反击,所谓的,不平则鸣。
20年前他在北京拍戏,“演一个比群众多几句词的群众,早上四点就从家里出来,下午将近五点才拍上我。那个戏给我两百块钱,这两百块钱我追了一个半月才给。”——对当时那个曾因没钱只能步行20多公里回出租屋的北漂来说,这200块钱,和他前半生里的许多事情一样,都得追着争着才能得到。
如今自然不需要了。2016年德云社成立20周年,一年时间里在五千人以上的体育馆演出111场,5000人以下的“小剧场”,400多名成员演了3000多场。这样的规模,当然是庆典,但又何尝不是扬威。
过去孜孜以求的“三百一场”,已经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事。如今郭德纲的相声帝国版图扩展到海外,上综艺不是主咖就是主持,电影可以继续客串,也可以自己执导——一切主动权看似都控制在自己手里。
现在他大可以选择“歇着”。2017年他在澳洲歇了半年,”不能再敬业了,再这样也不好,同行也得活着”。还叮嘱德云社,“各大卫视的春晚能不去别去,别的演员盼了一年了,商演是你,录像也是你,还让不让人活了。”
甚至,心态也渐渐“歇着”起来。当年讨薪那部戏的主角是曾志伟、曾宝仪父女。很多年以后,郭德纲可以和曾宝仪平起平坐地共话当年,当他聊到自己来之不易的片酬,曾宝仪说:“其实我们也没有拿到钱,那个制片方跑了。”
“谁都经历过这些。很正常,人都是从这活过来的,这是个资历。”45岁的郭德纲总结,公允持重,云淡风轻。
没意思和有意义
一见面,郭德纲就跟我们解释,“老了老了,打不动了。”采访里很多问题的终极解释,被指向“那会儿年轻”。
但叹老这回事,更像属于郭德纲自己可以感慨可以自嘲,但并不适合探讨下去的话题。如果我们就此较真,他也颇能够当场拆招——“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老了?”“就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。”“那你年轻的时候……”“你是说去年吗?”他愿意谈论的那部分“老了”,更接近于一种“什么我没见过”、“什么都没意思”的心态。“越来越柔和了。”他对我们总结。
按他自道,“老”可能是开蒙方式使然。郭德纲母亲身体不好,当警察的父亲出任务时,总把孩子搁在辖区里的戏院书馆。西皮流水急景凋年,一下午看遍王朝兴替;才子佳人帝王将相,两小时见识世道人心。人间总有一些规律一些领域不是个人奋斗所能掌控,道理他早就懂。
“我7岁学评书,9岁学相声,八十年代末又唱了几年的戏。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(台上演的)这么回事。我白天演一大奸臣,晚上演一大孝子,一天就能活俩人的一辈子。要说那都是假的,谁那是真的?你说呢?”

郭德纲演出京剧《嘉靖风云》
小孩子的游戏他没兴趣,一门心思学艺。“一块的孩子们人家玩得都挺好,就我在旁边跟孩子家长似的。”他形容自己,“打十几岁我就觉得自己挺老的。”
“那是少年强说愁。”我们接。
“愁到现在不知愁。”他回。
只不过是,道理都懂,意难平。目标先是“同行里面我们是最好最棒的”,后来是,“我们这些人每个都在,都很好”。被这点心愿拧巴到30多岁,“慢慢活明白了,大可不必。”
现在他的目标是,“不希望特别好,不希望出类拔萃,鹤立鸡群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鹤有多难受。”对相声业,并不想做执牛耳者,“你说全世界说相声的归我管,我都愁死,天天给他们念报纸,带他们上课,我活不了啊。”对德云社,也无甚长远规划:“没想干成百年老店,现在基本是哄着孩子们过日子,车没倒就向前走,只不过原来卯着劲,现在可以喘着气闲着。”至于对他自己,“该演出演出,该做节目做节目,该拍戏拍戏。谁说什么了——哦,说吧。”
“原来30来岁,没有不较劲的地方,什么都较劲。当都较完、较够了,我觉得没有意思了。”他对我们解释。
我们当然很乐意指出其他的例子:“那修家谱之后的论战呢?”
“有些东西不是争论,是必要的解释也罢,说明也好,是家谱一套的东西。”他解释。“在这篇(文章)之前,其实所发生的不愉快,都是有话没法说。这篇文章发完之后,我该说的都说了,以后谁也不要问我了,一个字我也不会再提了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终于解脱了,永远跟我没有关系了,就这么简单。
连原来的心头好,也渐渐变得没意思了。这些年里郭德纲收藏了一大批竹、木材质的文玩,“这个你看雕工多好,那个你看包浆多棒,一定是我的呀”。但发现自己“天天看着它,得累死”:“第一,不能丢了;第二,不能掉地上碎了;第三,天热不能给裂了;第四,我死了儿子可别把它卖了。”
到了现在,“就搁着,该玩玩,等有一天我快死之前,谁爱谁拿走吧。”
对如今的郭德纲,到底什么事情才是有意义的呢?“我有时候在书房坐着,吃完中午饭往那一坐,就看着帘子外面的太阳,就这么一点点往下走,我能坐一下午。很有意义,我觉得没有虚度光阴。”
又或者是,厨房里一堆洋葱搁着长芽了,他挑了其中最好的几个,找个花盆,搁点土,浇上水。”每天看着它,每天看着它:哎,洋葱长这么大的绿叶了,这就是意义。我就好开心。”大约是,到了这个年纪和地位,“有意义”这件事,跟欲望无关,跟存在有关。
狐朋狗友的交情
促成我们见到郭德纲的原因,是他执导的电影《祖宗十九代》的上映。很显然,一开始他也是奔着“意义”去的。两个多月前他曾发布长文,称自己长期享有“专拍烂片”的令名,其实不过是帮衬朋友、友情客串,“有机会我真拍一个,那个要是烂片你们再骂。”
但到我们采访时,“导部电影证明自己”的目标,已经变得“没意思”。“我作为导演我把这个东西拍完了,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”郭德纲当时对我们说,“你要是看得不淡,你就活不了了。我常说一句话:人活着不是为了看评论的——是不是很有道理?”

郭德纲曾客串电影《大话天仙》
当时电影尚未上映,但贺岁档的预售数字已经初见格局,同样的,这也是“没意思”的部分:“到了上映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跟艺术没有关系了。比如我们大批的观众说我太喜欢你的电影了,但是举着钱到电影院去没有你。有一场,凌晨三点半,你说怎么办呢?”
类似的意思,大年初一电影上映后,岳云鹏也在微博替师父表达过了:“不管怎么评价我们,我们都接受,但是这个排片……真的心疼我师父。”
我们能理解,“证明给别人看”对郭德纲来说,已经是越来越不重要的部分,但是,在拍电影的过程里,还是有与他指向自我的、有意义的部分。比如说,朋友。
郭德纲说自己是个“特别怵”社交的人。在各地演出时,主办方一开始总爱为他与当地显贵牵线攒局,”他们觉得就是吃饭,把郭德纲请来谈笑风生,多开心。不是那样的。但凡有一个外人,我一定会问:我走还是你走?迫不得已去了,也不说话,坐在那里想:主食什么时候能上。”“熬来熬去,熬的目的不就是熬成这样吗?真正的厉害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真正的厉害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。”言语里不是没有自得。
能跟他交上朋友的,都是和他一样,有自己的活法的人。比如他和吴秀波、孟非一起在澳洲成立了电影公司。我们很奇怪郭德纲的朋友交友范围之宽泛风格之广泛,但他觉得那只是因为,“都属于脾气比较各的”:“我老说仨神经病能玩到一块去,因为一样玩法,才会互相觉得这是自己人。不像大鹏他们,大家伙儿今天一起喝酒,明天过生日如何如何,我们很少参与这种事。”
郭德纲导演的《祖宗十九代》,大咖云集
在这个意义上,他的《祖宗十九代》,简直是朋友试金石:“我很感动的在这:33个超一线的咖,吴秀波、范冰冰、李晨、王宝强、大鹏……照理说得提前一年跟人说,人家才能给排时间,我都是临到跟前打电话:’下周五你有时间吗?来给我十天。’这搁别人怎么可能?人家要答应你,一定是推掉自己的事。但这33位真拿我当朋友,说来就来。”
这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交友之道。以理性判断,郭德纲明白自己没法当演员:演得再努力,都会败给作为相声演员的大众认知,“我不出戏,观众会出戏。”
但他还是一部接一部地演烂片,或许是因为,相比个人名誉,他更愿意给朋友帮忙。“谁找我帮忙,只要我能去就答应。”他也很明白别人在他身上需求的是什么,所以,对剧本、角色没要求,“就去三天,看什么剧本”;没人给说戏,他也无所谓;对方要是客气地给他署名出品人、艺术总监,他也笑纳:“如果我这点知名度能给人家宣传帮上忙,这不就是交朋友吗?”

郭德纲与好友吴秀波
他自己并非没有判断,臧否也相当直接:“去年特别烂的《欢乐喜剧人》电影,那个节目有三季我主持的。人家要拍戏,制作单位说您得参加一下,您是这个节目的灵魂。”然后他就加入了——因为情分,也因为自己的经历,见不得“一个人求到另一个人”。
“你没有珍惜羽毛之类的顾虑吗?”我们问。
“再怎么珍惜,也会有人骂你,跟你珍惜不珍惜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所以他交的朋友为了他的电影,也可以不惜羽毛。他颇为开心地讲起吴秀波对别的导演来说,属于那种“费劲费大了”的演员:“你找他,他的编剧团队先来了,先把你的本子改了,改成另一个故事”。但面对郭德纲,“什么都没有,连个故事都没有,让他把时间留出来。’哎好的。’完了经纪人找我一趟:跟您说两件事,第一,随便使唤,第二,别提钱。”
讲到这里,郭德纲面有得色:“这就是我们狐朋狗友的交情。”
我的故事得拍电视剧才够
我们相信,有时候郭德纲理解自己,参考的约莫是泱泱历史,一己悲欢一身荣辱完全无足挂齿。那种状态下的他,什么都不介怀,什么都不沾身。徒弟跟他告状有人骂他,“骂吧。”岳云鹏刚红的时候向他诉苦:“师父有人骂我。”“多吗?”“不多。”“回家熬着吧。”
这个郭德纲,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退休之后什么状态,过了40又开始考虑人面对死亡又是什么状态。“早晚的事,有来有去,很正常。不要惧怕,谁也躲不开。”今年他45岁,处世标准变成了“过好每一天”。“你再留恋这世间又怎样?你去逛逛故宫,你去看看长城,有什么可留恋?”
但能看开生死大事,却仍纠缠细枝末节。很多事情上,他的介怀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,比如我们问他,和电影行业接触获得了怎样的经验?“跟他们聊天我觉得好高兴。”
“高兴”指的是,他发现很多人都揣着明白说瞎话,“我一看就知道你心想什么,我都跟说相声的打了一辈子交道了,他们还在模仿那种说话方式。他们是没跟说相声的合作过,我跟你说说相声里边打不出1/10的人进入中国电影界,这帮人都得改行。”

郭德纲与德云社众弟子
很显然,说这话的郭德纲,不是“历史长焦下的郭德纲”,而是“自我经验中的郭德纲”:他对相声行业的积怨仍在,动辄拈来现砸一挂,远没有到“一切过得去”的程度——所有的高屋建瓴理性思辨,只帮助理解,不帮助治愈。
在另一个角度,也是他没有欲望扮演别人期待的样子,仍然要保留自己的脾气与好恶。就像说到自赏处,郭德纲难免要以“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这样深刻的人了”作结,那种溢于言表的得意,很容易联想到,他在台上说到精彩处略作停顿、等待笑声响起的时刻。
我们好奇的是,有没有一种可能,使这两个郭德纲妥帖贴合?“你没有想拍一部关于自己的电影吗?”“可以,但我这故事得等我80岁以后再说吧。”
前两年,电影《周恩来》、《邓小平》的导演丁荫楠曾向他建议,拍一个电影《郭德纲》。“我说你别闹了,我还活着呢。”
他觉得人活着的时候,最好避免“艺术家”、“大师”之类的舆论风向。“人们不太爱认同同时代的人很优秀,倒是爱夸去世的人:第一,人畜无害,第二,可以用他来打击一下现在活着的人。”
至于他自己,尤其不喜欢被尊到这样的位置上,“没有意义,也不好玩。”
“那你想过怎么讲自己的故事吗?”
“我这个故事比较复杂。我这个电影应该叫《我叫郭德纲》,得拍一系列,因为单纯的120分钟讲不了我这一辈子,可以挑不同的故事来讲,最适合电视剧。”
“怎么感觉你对怎么描述自己是有自觉的?一定会有一个故事留给大家?”
“那是肯定的,一定会的。”
郭德纲非常明白,就算自己彻底讲出了自己的故事,外界也仍然会有各种版本的传说。但对于这点,他可能是真的不介意:“别人怎么看我,怎么说我,这不重要,也挡不住。人活着无外乎就是让别人说,偶尔说说别人。”
大约就像,他与我们的这次采访一样。